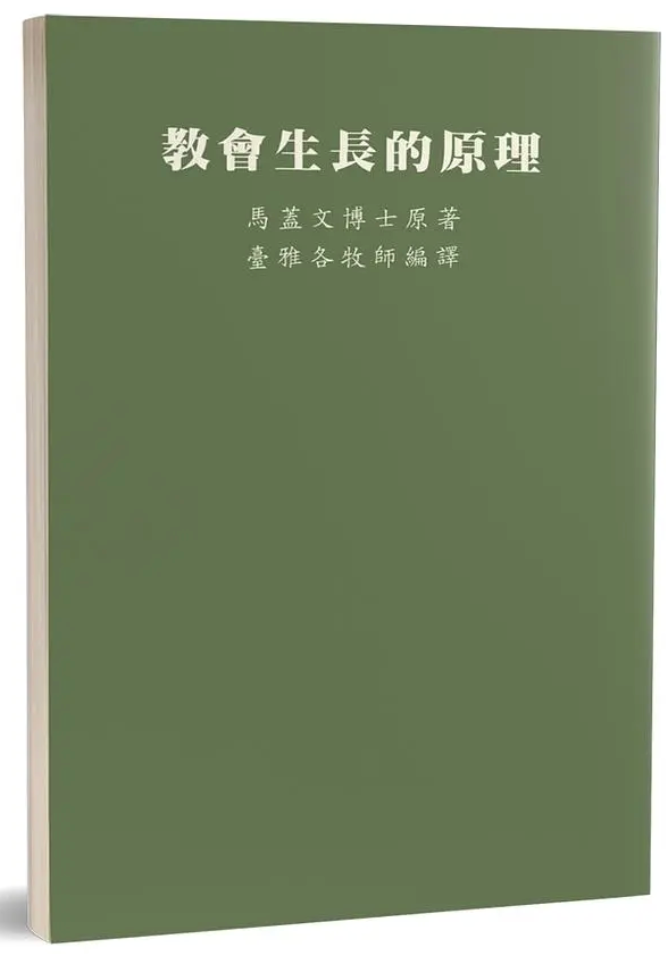
馬蓋文(Donald A. McGavran),《教會生長的原理》(Understanding Church Growth),Grand Rapids:Wm. B. Eerdmans 出版社,1990 年。332 頁。中譯本由橄欖華宣出版。
在中東晨跑時,我常看見當地人沿著海岸拋竿垂釣,耐心等候魚兒上鉤。有些漁夫似乎比別人更容易滿載而歸。我常想像這些早起的能手,帶著魚回到家中時,家人一定歡欣迎接。
然而,有一天我與一位當地人同跑時,我的看法改變了。他告訴我,海洋研究人員曾警告居民不要食用海灣裡的魚類——因爲水中含有大量金屬物質,食用這些魚對人身體有害。漁夫們雖然能把魚帶回家養家餬口,但他們真的該這樣做嗎?
類似的問題同樣適用於馬蓋文的著作《教會生長的原理》一書。這本書詳細闡述了教會增長的運作機制,這的確可能帶來增長。但問題是:今天的牧師和宣教士是否應該照搬這種方法?馬蓋文的方法論真的安全嗎?
馬蓋文痛心指出,二十世紀中後期的教會偏離了核心使命,陷入「普遍迷霧」中(55 頁)。他寫道:「宣教的首要且不可替代的目標是教會增長。社會服務固然蒙神悅納,但絕不能取代尋找失喪靈魂的使命」(22 頁)。他熱切呼籲教會重新聚焦在增長上:
大型佈道運動刻不容緩,這是福音前進的途徑之一。但正如本書清楚展示的,佈道運動必須以這樣的方式進行:能建立眾多新的教會,使許多新信徒成爲基督身體裡忠心可靠的肢體。」(xvii–xviii)
今天我們很容易對馬蓋文的憂慮感同身受。在許多教會中社會關懷仍然擠佔了福音事工的位置。對此,我完全認同馬蓋文的提醒:我們必須殷勤去尋找失喪的人,向他們傳講福音。然而,我不同意他所提出的具體做法。
在說明理由之前,我們需要先明白,這本書至今仍具深遠影響。
馬蓋文的思想,尤其是他強調社會科學對教會增長的價值,在 20 世紀 70 年代廣受認可。拉爾夫·溫特(Ralph Winter)的著作也在同一時期問世,他將宣教目標重新聚焦於「未得之民」。
溫特的民族誌(ethnographic,是一種寫作文本,它運用田野調查來提供對人類社會的描述研究。——譯註)視角幫助重新定義了宣教對象,而馬蓋文的社會學方法則提供了觸達這些族群的工具。過去難以想像的規模,如今似乎近在眼前。馬蓋文主張的一項策略,是不要在新信徒歸信後立即將他們「拔離」原有的社會關係,而是把他們視爲「橋樑」,藉此影響他們的整個社群。他指出,外國宣教士往往因爲「人們更願意在不跨越種族、語言或階級壁壘的情況下成爲基督徒」,反而築起了不必要的社會障礙。
這一理念後來被稱爲「同質單位原則」(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),旨在糾正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殖民色彩濃厚的宣教模式(163 頁)。馬蓋文詳細記載了「群體歸信」(people movements)的現象——在本土文化內部,大批人同時歸信基督。於是,宣教學界開始暢想新的增長可能性。溫特幫助聚焦宣教目標,馬蓋文則點燃了對大豐收的期待。《理解教會增長》一書也因此吸引了廣泛讀者,自1970 年起的二十年間三度再版。
直到今天,馬蓋文的方法仍深深影響著許多宣教策略家,儘管很多人未必熟悉他的名字。在本土化方法的極端實踐中,所謂的「局內人運動」(insider movements)鼓勵新信徒繼續保留在原有宗教社群中,以期發揮更大影響。這種思路可以追溯到馬蓋文的「上帝之橋」(bridges of God)理論和「家庭網絡」增長模式,其中尋找「平安之子」是關鍵。支持這種做法的根據常見於《馬太福音》第 10 章等經文,但其背後依然延續了馬蓋文的「同質單位原則」。
即便在非宣教語境中,馬蓋文的影響依然顯而易見。西方的「吸引式事工」往往圍繞年齡、階段、興趣等自然的親和力來發展小組。其邏輯與馬蓋文的方法一脈相承:只要減少社會學層面的阻力,教會、運動或小組自然會增長。畢竟,物以類聚,這理應成爲增長的有效途徑。
回到捕魚的比喻,現代的事工藍海中幾乎處處瀰漫著馬蓋文的影響。我們在不知不覺間,把他的社會學理論視爲教會增長的關鍵。
但問題是:在這樣的水域捕魚真的安全嗎?只要教會增長,就不會出錯嗎?
在這片水域裡,有兩種「外來元素」使這種增長弊大於利:
對馬蓋文來說,聖經的權威已經被結果取代,而他似乎並未意識到這一點。他寫道:「教會增長源於合乎聖經的神學與忠心。它大量借鑑社會科學,因其始終發生在社會之中。它不斷追尋上帝賜下增長的實例,然後追問:究竟哪些因素蒙祂祝福,從而帶來如此的增長?」(xiv頁)
請注意馬蓋文如何把「忠心」與「結果」緊緊捆綁:忠心因帶來增長而被肯定。畢竟,神不喜悅「徒具形式的追求」,即看不見果效的努力(6 頁)。換言之,凡能帶來增長的因素,就是蒙神認可的「正確因素」(132 頁)。這種邏輯在當代教會增長論者那裡常被包裝爲一句俗語:「瘋狂就是重複做同樣的事卻期待不同的結果。」這也是爲什麼他的書中充斥著案例研究——以可見的果效來論證「目的正當化手段」。他甚至說:「教會增長就是忠心」(6 頁)。這正是典型的實用主義。
請別誤會:我們都渴望果效。但這裡張力在於方法,例如所謂的「真實因素」——既可能確保收成,也可能腐蝕收成。這正是其中的危險所在。
公平地說,馬蓋文在書中偶爾也會提醒讀者不要過分依賴方法。但從整體來看,他的書仍在高舉方法論。他說:「緩慢的進展本身既非聖經教導,也非屬靈表現。有時必須忍受,但沒有理由將其奉爲圭臬」(121 頁)。然而,諷刺的是,他整本書卻在高舉那些能迅速產生果效的方法。他勸人不要神化方法,但他卻用「神的印證」作爲方法合理性的證明。
馬蓋文對《使徒行傳》的解讀中,「神化」那些立竿見影的方法的傾向十分明顯。《使徒行傳》敘述了早期教會在猶太人中擴展的過程,但可悲的是,隨著外邦教會的興盛,猶太人的抵制卻日益加劇。馬蓋文把責任歸咎於哪裡?真正阻礙增長的因素又是什麼?
然而,當大批外邦人成爲基督徒後,對猶太人而言,作基督徒往往意味著離開猶太民族,融入一個由多元群體組成的社會。接納外邦人反而形成了種族壁壘。合理的推測是:當作爲基督徒意味著要加入充滿外邦人的家庭教會,並參與「愛筵」(甚至偶爾會有豬肉上桌)時,潛在的猶太信徒因種族和文化隔閡過大而痛心離去。從那以後,猶太人普遍拒絕福音(169–170 頁)。
換句話說,耶路撒冷會議錯失了「社會學的機遇」。他們的認知盲區導致錯過了猶太人信主的「潛在收割」,並爲近兩千年的抗拒埋下了禍根。馬蓋文哀嘆這是一場收割的悲劇,而不是頌揚一間多元教會中神恩典的勝利。
如果社會學的壁壘真是猶太人抗拒的主要原因,那麼《使徒行傳》前幾章中猶太人歸信的真正因素是什麼呢?在馬蓋文看來,彼得似乎正好應用了這種「社會學祕訣」:
教會贏得了那些可贏之人——趁他們還可以被贏得之時。倘若五旬節那天彼得爲了贏得外邦人,就要求所有潛在的歸信者在飲食、婚姻、敬拜和傳道上都實行包容,而使徒們也立刻像對待猶太人一樣,把同等的精力放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地的外邦人身上,那麼最終成爲基督徒的猶太人將屈指可數。(29 頁)
你看出這個邏輯了嗎?五旬節就這樣被解讀成古代社會學的興起與勝利。在馬蓋文的視角裡,「同質性」帶來了猶太人的豐收,而「異質性」(heterogeneity)則阻礙了《使徒行傳》15 章耶路撒冷會議後的收割。聖靈所成就、原本超越人力的神蹟,竟然被社會學的規律所取代。
這正是水源受到污染之處。馬蓋文的釋經始終被他對「成果」和「同質性」的先入立場所支配。這讓我擔憂:他並不是順服聖經本身的教導,而是利用聖經來強化一種實用主義、受社會學驅動的教會增長模式。
然而,聖經早已指出:當福音的種子落在剛硬的心田時,即便是忠心的傳道人,也會遇見沒有果效的聽眾。這才是保羅對猶太人抵擋福音的解釋。他對聽眾說:
聖靈藉先知以賽亞對你們的祖先所說的話是不錯的。他說:
「你去告訴這百姓說,
你們聽是要聽見,卻不明白;
看是要看見,卻不曉得。
因爲這百姓油蒙了心,
耳朵發沉,
眼睛閉著;
恐怕眼睛看見,
耳朵聽見,
心裡明白,回轉過來,
我就醫治他們。」 (徒 28:25-27)
我們對神的心才是癥結所在,而「同質性」並不是脫離罪惡的救主。
無論是保羅,還是耶穌在「撒種的比喻」中,都沒有把沒有果效歸咎於缺乏信心(可 4:1–20);他們也從未把豐碩的果效歸功於同質性(太 16:17;林後 4:6)。
同質群體中也許會有增長,但如果這種增長必須依賴同質性,那麼自然的手段就取代了超自然的作爲。一個因同質性而被接受的「福音」,不會使人真正擁抱多樣性。馬蓋文雖期待教會最終成熟爲多元且合一,卻未察覺:那本應打破社會隔閡的福音,已被人挾持。最終,這些毒素會摧毀我們真正渴望的成長。
這並不是哀嘆福音在大學生、年輕夫婦或偏遠島嶼未得之民等同質群體中的果效。我的憂慮在於馬蓋文的預設:所有增長都等同於忠心,而同質性是開啓增長的關鍵。對他而言,「不阻礙聖靈、不限制教會增長的正確方法」就具有權威性(142 頁)。方法已經取代了神蹟。正因如此,他最終誤解了真正的教會增長,把可見的果效與聖經所說的忠心混爲一談。
這也不是說馬蓋文的觀察對讀者全無益處。但讀者必須謹慎,就像中東的漁夫一樣:外來元素已經滲入港灣,這片水域終究是不安全的。
譯:DeepL/STH;校:JFX。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:Is All Church Growth Good Fruit?